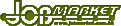我接過手機走到岸邊,電話一頭傳來丘醫師的聲音,他把聲音壓低了,但我仍感覺到他的緊張:「陳醫師,你那個開完腦瘤的病人意識在這個早上開始變差了。」我的心往下一沉,說:「昏迷指數幾分?」丘醫師說:「十一分,今早八點開始不講話,意識昏睡,因為血壓一直很高,他們叫我來看,我知道你在放假,但我覺得應該要通知你。」我放下電話,心裏頭比昨晚的狂風暴雨還要亂,我先和老婆商量,從這裏趕回醫院要兩個小時,還要花一個小時打包拆營帳 …… 我走回溪裏,溪水涓涓沖着我的腳,突然覺得好冷,小孩還喜喜鬧鬧的堆着石頭,兒子看我回來了興沖沖的向我走來,也許是我鐵青着臉,他問道:「爸爸,怎麼了?」我說:「兒子,爸爸要回醫院。」
「爸爸要回醫院。」這句話肯定是我小孩童年的噩夢。多少次因為這句話把我和他們硬生生的分開,念故事的時候、正在吃着晚餐、打着乒乓球、《侏羅紀世界》看到一半、背着女兒在游泳池,然後我就匆匆的拋下他們,他們會跑到玄關隔着鐵門哭喊:「爸爸!爸爸!你不要走!」慘兮兮的彷彿在送行易水旁的荊軻,偶爾鄰居還會探出頭來窺看這家子到底發生甚麼事?
我永遠忘不了的是兒子那時就站在溪水中央,當他聽到「爸爸要回醫院」時,時間彷彿剎時停住,笑容僵在他的臉上,像一隻受驚嚇顫抖的小貓,任由溪水拍打着他瘦小的身體,我看到淚水在他雙眼中慢慢的滾動,然後,就像有人突然啟動了開關,他放聲的嚎啕大哭,哭聲驚動了一群溪旁的水鳥,啪啪啪的飛上了樹梢。女兒見狀跑到哥哥的身邊,兒子在她耳旁輕聲的說了些話,我相信一定是那句可怕的「爸爸要回醫院」,頓時兩兄妹在河水中依偎在一起,抱頭痛哭。青山依舊,流水潺潺,所有的良辰美景,一忽兒的在我眼前崩塌。
一路上沒有聲音,沉默是有毒的藤無止境的蔓延,老婆小孩都睡着了,沿途盡是孤獨和荒涼。一直到檳城後我再次的拋妻離子直奔醫院。突然切換的場景叫我一時無法適應,病人已無意識的躺在床上,昏迷指數降到八分,瞳孔開始放大,腦部電腦斷層顯示出原本切除腦瘤的地方再次出血,我覺得喉嚨很乾,想吐。我通知手術室,必須趕緊把血塊拿掉。家屬在加護病房外等候着,他們都是善良的人,焦慮的聽着我的解釋,我簡單扼要的說明病人的情況以及手術的必要和風險。就在病人被推進手術室之前,我拍拍病人丈夫的肩膀說:「放心,我會盡力。」(待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