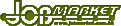醫院規定醫生每一年都要做一次常規的身體檢查。所謂的常規就是一般的抽血、心電圖和胸部X-光,不會太複雜,這種例行性的檢查就好比政府官員例行性巡視溝渠一樣,大雨來了結果還是照樣淹水。
我從不把這種檢查當一回事,既然是規定,自然就交差了事。醫生打從心底就有一種錯覺:只有病人會生病。我們習慣把醫生和病人硬生生的划分在兩個不同的圈圈裏,始終不承認原來兩個圈圈也會出現重疊的交集。早前,我完成了今年的檢查,心裏壓根兒沒把它放在心上,一頭又鑽進了忙碌的臨床事務中,直到開完最後一台手術,我接到放射科何醫師打來的電話。
「如果有空,能不能過來我辦公室一趟?」一如所有在昏暗不明的小房間打報告的放射科醫師,講起話來也是陰陰森森。我換好衣服走進何醫師的辦公室,他摘下眼鏡,指了指前面的椅子叫我坐下,我說:「怎樣?」他打開電腦,把螢幕轉向我,若大的肺部X-光出現在眼前,我特別注意到右上角處清晰的印着我的名字。
「我發現這裏好像有個東西。」何醫師指着右上肺葉處,一小撮的亮點躲躲藏藏隱匿在肋骨的後方,約
我應該如何描述,才能闡明我那個下午的絕望呢?我不知道如何離開放射科的,像路邊隨意被丟棄的塑膠袋,被風揚起漫無目的的飄着,不知不覺走到醫院外頭,當頭的烈陽照在臉上,帶來的不是暖意,反而是陣陣的冰寒。我想到家人,稚幼的孩子,應承過長相廝守的太太。
我閉起眼睛期盼阻斷所有的雜念,卻無法像關掉惱人的手機般簡單,大量的訊息不斷湧進腦海,長期練就的專業不厭其煩的提醒我,肺癌的五年存活率只有區區的18%,人生跑馬燈一幕幕的閃爍一忽兒的就把我帶到盡頭,我現在才知道,原來醫生不只會生病,而且更貼近死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