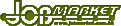我決定在事情還沒有一個定論前保守着這個秘密。報喜不報憂,沒必要把不確定的苦惱加諸在親人身上,我給自己畫了一個圈,把失意、憂慮、惶恐、全扔進生活泡泡裏,摘下醫師袍,我成了一隻負傷的困獸。第二天,我私詢了院內的胸腔內科醫師,他翹着二郎腿咬着筆屁股看着X-光片,沉默良久良久,我屈坐在他面前,從一位專科醫生不斷的萎縮再萎縮成了一球病人,我發覺我看他的眼神竟然有一種小狗偷瞄主人的膽怯。他眉也不揚的笑笑,若無其事的說:「是好是壞,做了PET CT scan(正子電腦斷層掃瞄)就知道,我等一下寫封介紹信給你。」我心想當醫生怎可以這樣冷漠,原諒我那天忘了帶修養出門,心裏暗地詛咒他:「期待你哪一天腦袋生了一粒瘤來看我。」話是這麼說,當我接下他的介紹信時,奉承得就像接下聖旨,只欠沒有跪下。
我來到指定的某家私人醫院,遞出介紹信,從此正式成了一個病人,編號是88561。我隔着防彈玻璃般的壓克力帷幕辦住院時,醫生光茫早已消失殆盡,脫下白袍後不過是一介凡人,這裏沒有人認識我,和醫院大廳熙熙攘攘的芸芸眾生一樣,這一秒踏進了醫院,下一秒也不曉得出不出得去。不管肺裏頭那一顆東西是不是癌,但生病的無助早已像癌細胞一樣肆無忌憚的蔓延。我趟在病床上,旁邊高掛着一排布廉。延着插在手臂上的輸液管,我看到高掛的生理食鹽水一滴一滴的墜落,像生命的沙漏細數着生命的終結,我趕緊把視線移到別處,要不然還沒病死就已經被嚇死,哪知道目光所及盡是蒼白的天花板,上面我看到歲月暈染的泛黃以及靈魂乾枯的水漬,天花板是病人一本看不完的書,也是臨終前穿透渾濁的雙眸投射在視網膜上最後一幕影像。一位瘦小的馬來護士把我推到了正子電腦斷層掃描室,這是一種偵測打入靜脈的葡萄糖正子(FDG)在體內和器官的分佈,以診斷腫瘤是惡性或是良性的檢查。整個房間是峇里島──監獄的設計,四面銅牆鐵壁,上面是黃澄澄的鎢絲燈,光線昏暗得可以放映電影,空調歇斯底里的開到最大冷得我直打哆嗦,如果這時轉開音響播送大悲咒就真的太完美了。醫院已經夠恐怖,有必要把這裏弄得像陰曹地府嗎!小護士叫我從床上下來,我的背部剎時一陣沁涼,不知哪個笨蛋設計的病人袍,套在前面,後面卻是開叉的,露出了光溜溜的屁股,冷得八月十五起滿了疙瘩。我已經顧不得咒罵,胃一陣抽搐想吐,躺上掃描器硬棒棒的床板上,我被送進了一個圓桶裏,上面有一圈滾輪閃着光不斷轉動,我有一種被送上巴士底獄斷頭檯的沮喪,不知道待會被拉出來後頭還在不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