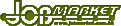在圓桶裏面待多久,就是在棺材裏面待了多久,硬板把我拉出來時,我彷彿看到耶穌光,像從鬱悶的子官穿過產道初次探出頭來的新生兒,忘了放聲大哭,只是驚恐的大口喘氣。我全身虛脫,馬來小護士把我扶到病床上,輕輕的替我蓋上被,還溫柔的告訴我檢查已經做完,我相信看到了天使,也終於知道天使不分黑白。
兩個小時後,一個大鬍子的印度醫生來到我房間,我曉得審判已經到來。接下來我就會被推進手術室切掉半個肺,以後別說打球,連上廁所尿尿都會喘,之後開始化療和放射治療,頭髮牙齒和指甲開始剝落,唯一的幸運是我已經有過睡棺材的經驗。
「是良性的。」他說。甚麼?我瞪着他,嘴巴張成了一個大窟窿,不相信我中了樂透。「是良性的瘤,但我建議要繼續的追蹤。」我的眼淚不爭氣的湧了出來,注視着醫生性感的嘴唇,顧不得扎人的虯髯,我好想親下去。離開醫院已是黃昏,我開着車看向遠方,第一次發現夕陽是如此的美麗,空氣是如此的甘甜,我想到小孩和太太,我只想趕快到家給他們一個抱抱。
事情已經過了一年,記得有一次經過病房,我看到一個老伯在床上不斷的顫抖,他床頭的名牌標註着他患的是胃癌。我向護士多要一張棉被給他披上,他笑笑和我道謝,我指着他手腕上戴着的號碼說:「不客氣,我曾經也是那個88561。」